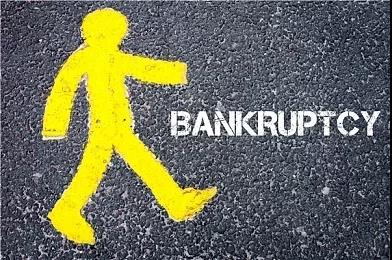二 破产优先权探讨的体系化检视
破产优先权制度,因符合实质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理念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然而由于破产程序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往往意味着必然债权人要做出牺牲,因为对债务人企业有限资产的分配往往属于“零和博弈”,过多分配给优先权人必然意味着普通债权人可获份额的减少。如果说优先权配置不合理,极有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反之长远影响社会福利的提升。
有鉴于此,为使破产优先权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公共利益倾斜保护的制度价值,同时又避免矫枉过正,应当对破产优先权进行体系化衡量。
笔者认为,前述论争中的破产优先权往往局限于个别优先权权利基础及顺序的探讨,这种探讨往往是就某一特殊利益或者群体保护的重要性探讨,而忽视对既已确定的破产法理念和社会经济实践指导下的宏观探讨,即个别优先权配置及调整充分性的探讨,也即在破产法整体框架下体系化衡量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
01、优先权权利基础与破产
法的理念的协调往往厚此薄彼
如前所述,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对权利基础的探讨较为全面,也即对任何一债权是否具有泛化的优先权依据有分析,使得论者在新近的关于优先权的争论都有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的探讨多集中于必要性或重要性的探讨,仅就某一具体的债权是否有必要上升为优先权的探讨,而忽视对个别债权适用优先权充分性的探讨,例如基于拖欠劳动者债权数额庞大的数据和事关民生稳定而主张职工债权当有超级优先权,或是受到社会典型案例的影响而主张建立人身侵权债权优先权的新型优先权,其局限性表现在:
1
一是宏观上欠缺对破产法宗旨实现的衡量,仅对个别债权的探讨优先权,往往体现的是某一特殊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利益,而因其重要性上升到优先权的地位,往往忽视《破产法》所主张的公平分配债权和保护“诚信但不幸”的债务人的宗旨,使得《破产法》仅成为债权分配的“破产清算法”,而使债务人财产成为债权人的“公共鱼塘”,导致债务人企业通过重整和和解复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二是微观上忽视对其后位优先权及普通债权的比较分析,仅对重要性的探讨论证其必要性在逻辑上不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还不能忽视对充分性要件的分析,在破产法领域,赋予某个债权优先权或调整优先权顺位其影响是双向的,简言之,还会造成被调整的后位优先权以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因而与其它债权比较分析显得尤为必要,也是论证某一目标债权是否有优先权地位的充分条件。如若缺少这一充分性论证,加强了某一目标债权的地位,却忽视了对其他债权及其背后业已经过考量的价值的保护,难免避重就轻、顾此失彼。
02、《破产法》实践效果不甚明显,
更需要彰显破产保护的理念
现行《破产法》出台至今已逾十年,然而由于破产法理念尚未深入得到贯彻,施行效果并不明显,破产率远低于一般国家,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就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的数据看,2003年-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破产案件40483件,年均下降12.23%。,直到2014年呈明显下滑趋势;其中法院宣告案件占比32.55%,宣告破产比例也逐年下降。
2014年我国适用破产程序的企业数量每年不足美国的6%,仅为西欧国家的1%;每千家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显著低于西欧国家平均70户的数量。
尽管随着《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治理僵尸企业大潮中,破产案件受理和审结数量有所上升,2016年受理企业破产案件5665件,比2015上升53.8件,审结3602件,比2015年上升60.6%,其中重整案件525件,比2015年上升43.4%。
然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破产法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能受到较大限制,具体体现在:多数企业退出市场并非依据司法破产程序,而是依据工商行政手段吊销、注销的企业的机制,这使得很多企业并没有经过债权债务清理而直接退出市场;破产司法程序启动者主要是企业债务人而非是债权人,理由在于一方面多数债权人无法全面了解履行能力、经营状况及资产负债等债务人清偿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进入破产程序受偿债权额往往较少,债权人更倾向于通过个案诉讼而非破产程序实现债权。
很多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偿债能力的企业并未进入破产程序而是未经过债权债务清算自由退出市场,破产法的实践仍未实现由债权人主导的破产清算法转变为多方主体利益平衡主导的破产保护法,破产保护的理念仍旧未在商业文化中得以植入。
然而,优先权的设立及存续往往以牺牲后位债权人或者普通债权人受偿能力的可能性为代价的方式,用以平衡特殊群体债权人的利益,其性质是一种特权,过于泛滥的优先权更会加深《破产法》是“破产清算法”的偏见,使得债务人企业的财产成为“公共鱼塘”,“僧多粥少”的局面令许多债务人企业面临危机不愿意启动破产程序,后顺位债权人及普通债权人更愿意提起个别诉讼实现债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企业财产,反而对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人也不利。
此外,破产重整和和解程序的制度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债务人企业的危机往往难以挽救,仍不利于彰显破产保护其他债权人以及债务人企业自身理念。于此,妥善和谨慎分配和调整优先权,对彰显破产保护的理念显得尤为必要。
03、破产优先权渐趋衰弱,
特殊群体法益保护机制日趋多元
在比较法上,职工债权优先权的趋势呈现衰弱趋势,德国于1994年在《支付不能法》第39条和第123条取消职工债权优先权;日本在2004年修订的《日本破产法》第149条规定优先权数额由之前的6个月限制为3个月工资,类型限制为未支付工资和退休金;巴西在2005年出台的《巴西破产法》规定职工债权优先权由之前的不受限制变更为不超过150个月的最低基本工资(约为13000美元)。
外,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瑞典、比利时、荷兰、印度都对职工债权予以限制,主要包括权利主体、优先受偿数额与期间以及优先受偿的职工债权类型。
与劳动者的职工债权相似的是,税收债权在破产优先权也呈现衰弱趋势,税收优先权肇始于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当时的口号是“即使债务人死亡,国王仍得优先受偿”,是英国国王特权象征,但是经过多伦博弈、多部法律与案例重塑,1982年英国审查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在《破产法与实践》中主张取消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债权优先权,并主张在保留的税收债权类型中予以优先受偿债权期间的限制。
德国、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取消税收债权的优先权,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分别在税收债权优先受偿期间与类型上作出限制。除此之外,许多国家主张对现有法定的优先权予以限制,并对优先权的认定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对于需要优先权予以特殊保护的群体利益,更倾向于通过探索相应的责任保险、赔偿和救济基金、责任人追索等机制予以保护,从而兼顾债权人利益平衡以及挽救企业债务人危机。
目前,我国正在上海和深圳实施欠薪社会保障基金的试点;针对于大规模侵权现象的发生,也能通过行政机制或者团体协会自治的方式予以快速便捷的救济,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协调22家责任企业设立11.1亿元的赔偿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如若优先权的设定及调整过于泛滥,在我国与优先权趋势日渐衰弱的国家经济交往时,在国际破产法领域难免会出现优先权适用纠纷的困局。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元的保护机制使得保护特殊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的优先权配置或者强化缺乏一定的充分性条件。
一言以蔽之,现有研究或集中于某一具体类型的优先权,仅试图建立或梳理“小而全”的特定破产优先权类型,其弊端在于难以贯彻和伸张破产法的宗旨和原则,并未明确破产法的整体发展方向或趋势;抑或是梳理现行立法既定的或未定但尚属争议中的优先权类型,试图建构起“大而全”破产优先权体系及清偿顺序,其弊端在于研究精力分散,论点缺乏清晰明确的论据做支撑,结论往往不具有实践效用而颇有说教之嫌。
就破产债权分配而言,在规范性论证某一破产债权优先性及其顺位时,需要谨慎对待,应当具有足够且充分的理由,既要对重要性这一必要性要件考量,又不失对破产法宗旨和原则以及合理对待其他债权等充分性要件予以考量。